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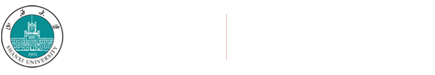
信息来源:《中国高校科技》2021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1-09-06
摘要:学科治理是现代大学内部对学科事务的引导、协调和规范,也是学术治理在学科领域的外显形式。“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实现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然成为全面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然而,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交织下的学科治理,存在权力关系错位和过度规划干预等现实问题,导致大学行政化制度下的学科治理面临资本化、功利化倾向和向壁虚构等现实困境。实现大学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需结合学科知识与组织的双重属性,突破学科治理的组织瓶颈,明确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建立以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为核心原则的学科治理自主决策主体和学术共同体,以构建相互承认、尊重、共赏的合作型学术治理权力结构,实现学科治理与学院治理的有机耦合。
关键词:学科治理,“双一流”建设,治理能力,学术权力,行政权力
学科既是现代大学的基础组织单元,也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促使各大重点高校将学科建设纳入办学战略的决策核心,而普通高校则期望通过优势学科建设提升自身的学术地位和综合竞争力,从而在国家“双一流”建设中谋求更多政策红利,实现办学实力和办学质量的“弯道超车”。学科建设发展是诸多资源要素整合与转化的过程,其中,学科治理能力是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其主要功能在于界定学科建设基点和边界,以合理配置资源,把控学科建设方向及发展特色,组建完善学科人才队伍,夯实学科组织基础,构建决策机制等。结合学科治理理论逻辑,重塑高校学科治理权力结构,厘清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边界,巩固学科治理组织基础,强化基层学科组织建设,构建学科文化生态,提升学科治理文化动力,最终实现“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破解学科治理困境、保障学科有效建设与良性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
一流大学建设需要以一流学科建设为依托,学科建设与发展水平是体现大学办学质量与自身实力的关键要素。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核心,涵盖大学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建设周期长、成果见效慢的系统工程。构建科学高效的学科治理体系,探寻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是有效推进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前置条件。学科治理是促进学科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实现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动高等教育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在学科治理体系中,学科关系到学术共同体成员价值认同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制度规范的确立,为学术共同体开展学术交往互动提供了制度支持,凝聚了学科治理合作型权力结构的动力,是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内生动力源泉。现代大学学科治理往往被置于大学治理的整体框架下,涉及政府、高校、学者、社会等多元利益主体。实现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综合考量不同主体的利益表达与权力交互,设计出适应治理主体需要的制度体系和文化环境,明确其治理价值取向、治理内容、治理责任和运行逻辑,保障其治理行为的合法性,捍卫学科自治和学术自治的核心地位。善治是现代学科治理的最终目标,在民主共意的学术语境下,各项学术活动开展和学科建设行为都需要依托于系统、科学的治理体系,良好的学科治理能力能够调和实现学术自由和运行秩序之间的合作型规制构建,激发学术共同体成员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协调、提升院系与学科的综合治理能力,最终实现从合法治理到善治的转型,形成学科治理自发自生的良好秩序。
大学作为学术组织,构建学科的组织化与制度化体系是保障其知识生产的关键内容,学科顶层设计与发展战略规划、学科团队组建与运行、学科资源配置与优化、决策机制构建与完善、学科文化培育与发展、学科建设成果评价与激励等内容,均为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内容和关键议题,构成了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学科治理互动涉及学科、院系等多个层级,对于学科治理内容及学科资源配置方式的处理,相关重大决策须经由特定组织和规范程序进行,由此建立基于学术自由与民主原则的学科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调和决策机制,以成员集体“行会式”决策为核心,构建合法合理的学科治理权力结构,实现学科治理与学院治理的有效耦合。学科制度化和组织化整合了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通过构建高效协商的对话机制有利于实现学科治理能力的提升。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多元学科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良好的学科治理并非由行政领导或学术领袖单一控制,而是由符合学科共同体成员价值取向和共同体认知的多元治理主体构成。当学科治理主体单一化且缺少与其他主体的互动交流时,学科建设则往往沦为少数人学术霸权或技术控制的工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学科治理进行互动对话,形成开放、多元、动态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机制,能够达成有效的学术认可,疏通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价值诉求的对话渠道,形成学术共同体协商共意的治理共识,以保障学科治理行为的正当性与有效性。
二是学科治理制度的自反性重塑与创新。现代大学的发展逻辑根植于现代社会的运转逻辑,同时也在催生新的社会逻辑,而应用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正是不同学科治理模式主导下学科文化及大学文化的重塑。学科是大学发展与提升的根基,良好的学科治理不仅需要以知识生产创新为驱动,也需要治理制度的自反性重塑和创新动力。因此,需要结合社会发展的外部需求和知识生产的内部动因,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重塑学科文化,形成跨学科交互对话机制,构建多元化和开放型的学科治理理念,鼓励学科交叉和多样化发展,实现跨学科知识生产传播与社会转化应用的有效衔接。
三是治理重心下移,捍卫学科自治权力。学科由知识产生,最终演化为组织化形态,依托集体智慧完成知识生成体系的进化与更新。基于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自治能力和契约精神,学科治理已经形成了合意协商秩序,其借助于高度专业的学科组织来运行,排斥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倡导基层学科组织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理过程,共商决策,实现学科治理重心下移。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科治理权力取决于其自治能力和契约精神,在合意治理机制下突破组织短板因素,建立学科资源公共化理念,共同履行治理责任,参与到学科发展规划、资源整合配置和跨学科交互等治理过程中,实现学科治理组织的实体化及自主治理与决策的战略目标。
四是学科治理文化生态的包容环境。大学学科的本质是学术共同体,其主要活动为教学、科研等学术行为,其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学科知识生产与发展体系的完善,而其知识生产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理念与思想规范,构成了学科文化的基本内涵。学科文化是大学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高校行政化生态中的行政文化,其能够构筑阻止行政权力过度渗透的“文化防火墙”,指引学科治理的发展方向。实现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培育以学科文化、学术文化为主导的学科治理文化生态,均离不开学科治理主体对学科文化的价值体认与悦纳包容,同时要强化学术共同体成员对学术活动的价值认同和归属感以为其治理行为赋能,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二、学科治理现实困境的核心矛盾溯源
(一)学科知识属性与组织属性的双重交织
人类对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探索结果的总和形成了知识,而学科作为知识集合体,是其自生自发于知识演化的必然结果。学科自大学诞生后开始萌芽并逐渐发展巩固,其构成了大学的基本单元和知识生产组织结构,具有系统化和逻辑化的基本特征。当前,学术人在实践中已经建构出完整的学科话语体系,其中包括以客观形态而存在的学科组织,以及作为虚体观念而存在的知识生成演化逻辑,学科的知识和组织双重属性愈加显著,成为贯穿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的主要脉络。从知识属性来看,学科建设与发展遵循知识产生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具备知识生成、保存、更新、传播、转化、应用等功能。科研成果、学科带头人、学科声誉等知识生产、传播、创新转化能力,共同形成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学科队伍建设、学科管理体制、学科建设理念、学科政策导向等组织制度因素,则是引导、把控学科正确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的关键。知识属性和组织属性交织成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双重动力,而在实际建设和管理践行中,高校学术问题往往会受到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行政意志在压缩学术权力行使空间的同时,亦限制着基于知识属性逻辑的学科发展动力。
学科治理是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所建立的学科事务决策结构体系,在特定治理环境下凭借学科决策权,通过特定方式作出影响学科发展的相关决策,其重大决策往往决定着学科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和学科建设发展质量的好坏。学科治理本来应当遵循学科建设与发展知识和组织的双重发展规律,但在实际践行中,部分高校由于学科制度文化底蕴的匮乏和缺失,导致学科治理主体呈现出“官学一体”的总体特征:即行政官员掌握学科治理决策权力和核心话语权,导致学科组织的职能缺位,学科治理呈现出非组织化特征,重大决策不经由学科组织框架和必经程序共同协商,而是由领导者根据个人意志所决定。学科治理的非组织化特征严重背离了知识生产传播体系的普遍规律,亦导致学科治理重大决策缺乏程序正义,违背学科决策的民主共识,危害学术共同体的团体治理要义和学术民主精神,导致学科组织流于形式,学科治理严重失范。同时,学科组织形态往往表现为学科团队、系、院等高校基层组织,实质却是学术人基于学术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建制,其运行离不开学科资源要素的投入和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权力主张;学科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应用的有效转化,亦依靠学科组织在研究方向、团队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相关决策。学科知识与学科组织的利益交织,决定了学科治理的内生逻辑及运行机制,要求其必须同时兼顾实现知识生产与组织运行的共同善治,以组织运行善治为知识生产善治提供运行支持,以高效的学科资源转化效率与质量实现学科知识生产创新拓展的目标,坚持学科治理重大决策的学术本位原则和价值取向。
(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模糊
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战略的持续推进和深化,学科建设成为高等院校提升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关键抓手,其在承担大学知识生产创新拓展职能的同时,亦与大学学术声誉紧密联系。与此相对应的是,学科排名竞价、学科建设成果商品化、竞争行为功利化等驱利行为日益显现。面对“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学科建设功利化、商品化现象,提升学科治理能力已然成为重塑学术共同体、学术责任担当和恢复学科建设规范的必由之路。
一方面,我国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政府部门利用政策工具对高校进行宏观治理,较少干预校园内部事务,校长拥有校园内的最高治理权,其自身通常拥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管理权构成了其学术权力的来源,而学术权威往往被赋予更大的学术权力,掌握学术组织内部资源配置的决策权。大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权力逻辑的介入,以及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博弈,涉及行政领导、学术人等多元利益主体。与此相对应的是,学科组织的高度行政化往往导致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行使的空间,在科层制管理制度下,行政权力把控着学术资源的配置,过度干预学术事务,甚至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决策,导致学科治理行政化;以学院治理简单替代学科治理,会导致部分学术人利用自身学术权力掌握重大决策权,忽视其他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话语权,导致学科治理权力结构形同虚设,学科组织沦为行政工具。部分高校学科治理能力不佳甚至失效,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行政长官兼任学科带头人同时掌控学院治理与学科治理的决策权力,利益驱使下的学科建设沦为谋利工具,学术共同体的其他成员话语权、决策权失衡,导致学科资源配置效率和学科发展质量低下。
权力决定着学科知识的生产与转化,亦把控着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话语权。学科治理内容包括利用权力规划学科发展,汇聚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共同意志,确立核心话语主体以进行学科话语体系、结构规划、建设评估等相关决策。大学行政领导取代学术权威行使学科治理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交叉失范,往往导致学科治理制度体系失效,而学科治理行政化的根源,在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制度体系存在漏洞和组织化建设进程滞后,行政权力扭曲吞噬学术权力的行使空间,使得学术共同体治理文化缺乏有效发挥,最终将导致学科组织和学术共同体虚置并产生功利化倾向。因此,实现学科善治必须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边界,将实现学科知识的创新拓展作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强化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决策权与话语权,建立健全以学术共同体为核心的学科治理结构,优化学科治理过程。学科建设与发展应深入治理领域,尊重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权力,限制行政权力在学术场域的过度渗透。
三、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探索
大学的办学质量和综合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学术水平和学科建设质量方面,不断追求更高学术目标以诞生新思想、新科学和新技术。一流学科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动力支持,学科治理应以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知识生产创新应用为出发点,以对学科理论思维及知识演变体系更新作为矫正学科实践乱象的核心支撑,纠正行政功绩和谋利目的对学科治理的错误渗透。学科治理结构及治理过程是学科建设成效的决定性因素,对学科重大事务决策质量有深远影响,对实现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重塑学科治理权力结构,构建学科自治话语体系
学科治理需要依托特定学科组织和制度框架进行,现代学科治理处于大学治理的大环境之下,存在以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为各自主导的双重合法治理主体,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博弈,学科治理更是涉及多方利益。然而,学科是大学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只有充分尊重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科治理话语权和决策权,才能最终实现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现良好的学科治理,需要重塑学科治理权力结构,给予学科科学发展和自我净化的制度空间,避免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遵守学术自由、自治的治理理念,结合大学发展、学科建设和社会需求等多层次结构进行审视和规划,科学分配不同主体的治理参与度和话语权,使其拥有与各自权责地位相符合的学科治理权力,在学术场域的互动共生中达成共同治理的合作机制,形成合法合理的学术治理权力结构,完成学科自治的独立话语体系构建。
对于学科决策,应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民主科学决策机制,合理规划不同学科的治理权力主体的类型分布,预防学术霸权对相对弱势学科的生存空间的侵占,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模式,促进学科共同发展。针对关系学科发展的重大关键议题,可采取学科学者“行会式”决策模式,最大程度保障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决策权力和民主权利,通过成员共同讨论、协商达成决策意见,捍卫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突显学术本位的治理原则。此外,行政权力同样要为学科治理提供指导与保障,在捍卫学术权力行使空间和学科自治原则的前提下,应界定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和各自的空间范围,以实现两者的共生互动良性发展。
学科是大学的基础性结构,也是大学二级学院的生存根基。学院与学科为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学院为学科知识生产、传播提供制度保护和管理服务保障,由此,学科治理权力结构中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为依存和支撑的共生关系。由于学院兼具学术事务处理的职能,导致以其为组织载体的行政权力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学科治理的过程;学术权力既要掌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事务决策权和话语权,亦要兼顾学院与学科事务联系的微妙平衡。因此,在实行学科学者“行会式”决策模式的同时,应增设大学对学科自主治理重大决策的审查补充机制,在尊重学术权力行使和自主决策话语权的前提下,对冲突、矛盾之处加以沟通、协商和必要修正,以预防学术霸权行为,促进学科决策结果科学化。以北京大学学科治理模式为例,其在学科治理改革实践过程中,加大了学术权力在学科治理权力结构中的配置比例,通过建立健全学科组织,以保障学术权力合理合法的行使空间,加大学科带头人的治理参与力度,以提升学科治理决策的科学性;行政部门则对学科建设给予大力配合和有效支撑,履行着组建学科建设办公室、统筹学科建设等相关职能,形成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共生互动治理体系的良性运转,实现了学科治理和学院治理的有机耦合。
(二)巩固学科治理组织基础,强化基层学科组织建设
大学是高度制度化的组织,大学学科往往以学系、学院等基本组织形式为建设依托,但学院自身兼具行政和学术的双重属性,其治理与建设并不能与学科治理等同。学院治理除了承担组织学科教育教研等学术活动职能,其更主要的职能是院长负责制领导下的管理与服务等行政事务治理,且往往涉及学科层面的重大事务决策,以学术共同体为治理的组织载体,其主要功能为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故需在治理权力结构中明确学术权力的主体地位,遵循学科发展和知识生产的根本逻辑,采取“行会式”治理模式,构建基于学术民主原则、学术人为主体的决策模式,明确权责利益划分,修正学科治理实践过程中学院治理与学科治理相互混淆、行政权力主导学科治理等问题,规避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冲突,规范学科治理行为,切实维护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保障学术共同体成员在学科治理权力结构中的参与度、话语权和决策权,形成教授治学的良好传统,构建学者集体决策的扁平化治理结构。
学科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必须依托于学院化的组织系统和体制保护。基层学科组织能够强化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和价值体认,形成学术权力组织化和整体性合力,以捍卫学术人的治理决策权与话语权,提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过程中的优势地位,进而凝聚整合学科组织化效能,重塑学科治理权力结构,实现学科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的优化。学术共同体和学科组织建设是学科治理的权力来源和行使依据,正规化、建制化的学科组织,能够有效提升学科治理能力,满足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可建立“行会式”学科治理体系,经由民主决策机制遴选学科权威,明确权责划分及相应的考核机制,经过规定程序后进行任用。遵守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原则组建学科团队构建学术共同体,合力形成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为实现良好的学科治理巩固组织基础。同时,还应建立高于学院组织、基于学科设置的组织平台,实现大学层面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战略规划和学科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院系学科交叉融合。致力于跨学院的整体学科建设发展,联合创造互利、共进的学科发展环境,整合同类资源形成合力,实现学科规模效应,释放学科组织发展活力。建立基于课题项目或学术研究目标的教学科研基层组织团队,搭建信息互通共享平台,加速学科成果生产转化效率,优化人事考核制度和资源保障体系,保障学术共同体成员灵活参与、规划学科建设与发展。
“行会式”学科治理模式,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组织依托。制度能够有效规范组织行为,推动学科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利用制度巩固学科建设与发展成果,提升学科治理成效,有利于实现学术共同体、学科组织、学科治理制度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制度建设是对学科治理成果的确认和保护,对制度的不断改良和完善是巩固学科治理成果的必要措施。在学科组织和学术共同体专业力量在权力结构博弈过程中抢占先机后,建立健全学术自由制度保障体系,巩固学科治理合法性基础,建立起各级学科的学术权力组织,使之成为学科重大事务决策的行使机构,按照学科建设与发展逻辑构建科学的治理结构,并在实践过程中探索持续性的制度优化和改良,在适宜的制度框架下开展学术决策和学科治理,最终形成与学科治理体系高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三)构建学科文化生态,提升学科治理文化动力
Bailey认为,大学由受到不同文化所操控的“部落”组成。该观点生动而形象地表述了学科文化对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大学核心竞争力提升的规约功能。学科文化是大学学科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学科特有的思维理念和伦理规范,能够使基于共同的身份认同、学科价值理念、伦理规范和思维方式的学术共同体成员凝聚为一体,经其认同、吸收和内化后,转化成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文化意义,进而成为学术共同体成员自觉接受和认同的行为规范,形成其突破传统格局、创新发展的文化源泉。学科在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基于自身知识生产体系而诞生的价值理念和伦理规范,构成了学科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学术共同体成员价值体认和身份认同的文化成因和精神归宿,赋予其投入学科建设和学术活动的动力支撑。
学科文化的培育依赖于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合力,同时也依靠学科建设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在学科组织和学科队伍建设初步成型后,需要着力加强学术共同体成员内部学科文化建设,以培养形成全体成员共识的认知理念和学术信仰。在建设学科文化和学术文化的途径中,应重点发力使学术共同体成员认同学科组织的价值属性,使行政权力组织机构尊重学科自治权力,在学科组织和行政组织内共同形成尊重知识生产体系、尊重学科自治权力和发展规律的良好氛围,巩固学科治理合法性基础,为学科治理组织化、制度化建设提供思想支持。学科文化为学术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且为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构建了共建共享的治理价值理念,为学科治理涉及的多元利益主体达成治理共识提供了价值导向和文化诱因,因此,学科文化建设应成为贯穿学科治理全过程的核心要素。
学科治理过程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博弈和对话语权优势地位的争夺,离不开源自学科文化的合法性基础。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术专业话语权和学术权威,其在学科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与行政权力并行不悖却又格格不入,学科文化与行政文化之间的冲突屡见不鲜,在学科治理领域则表现为学术自由、民主原则与学术领袖专业权威之间的文化冲突。因此,为实现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需将学科文化生态培育置于学科治理的突出地位,培养学科共同体成员的文化自觉,以弘扬学科文化为己任,整治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功利性治理态度,倡导真理治学,注入批判文化元素,赋予学术共同体成员以使命感,不断矫正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价值规范,以文化建设化解学科治理困境和危机,构建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促进学科文化良性生长与发展,为学科发展与建设提供文化规范,确保学科治理科学化和有效性,探索出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文化繁荣路径。
主要参考文献:
[1]陈金圣.学科治理的基本依据、组织基础与运行机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3):7-13.
[2]陈亮.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双一流”建设的逻辑旨归[J].高校教育管理,2019,13(6):55-63.
[3]陈金圣,邹娜.论高校的学科治理[J].高教探索,2019(6):16-21.
[4]陈金圣.大学学科治理:现实语境,多元价值与推进路径[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9(1):62-68.
[5]杨岭,毕宪顺.学科治理视域下教授治学运行机制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9(3):87-94+125.
[6]方晓田,郑白玲,陈亮,等.以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现代化推进“双一流”建设(笔谈)[J].教育发展研究,2018,38(19):50-62.
[7]钟卫.应用型本科院校一流学科建设的三个向度[J].中国高校科技,2018(8):37-38.
[8]杨超,徐天伟.“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6):25-31.
[9]何晓芳.学科嵌入式治理:一流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制度逻辑[J].中国高教研究,2019(9):29-34.
[10]谢凌凌,陈金圣.学科治理: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核心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17,37(7):38-45.
[11]杨超.“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教师参与学科治理的困境及路径[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9):39-45.
[12]宋亚峰,王世斌,潘海生.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学科生态与治理逻辑[J].高等教育研究,2019,40(12):26-34.
[13]曾亦斌,王钊.“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行业性院校的学科生态治理研究[J].江苏高教,2018(3):25-28.
[14]叶逢福.我国大学学术组织内部“泛行政化”的识别、成因与治理逻辑[J].江苏高教,2017(8):23-26.
[15]曾维华,王云兰,蒋琴.大学去行政化的拐点: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J].广西社会科学,2017(1):205-209.
[16]朱德米,刘志威.中美一流大学行政化程度的测量与比较[J].复旦教育论坛,2019,17(3):31-37.
[17]彭秀丽.普通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表现及去行政化的实践构想[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7(9):43-46.
[18]BECHER T. The Significance of Disciplinary Differences[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1994(2):151.
作者:闫涛,天津工业大学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管理;曹明福,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刘玉靖,天津工业大学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管理。
来源:《中国高校科技》2021年第6期